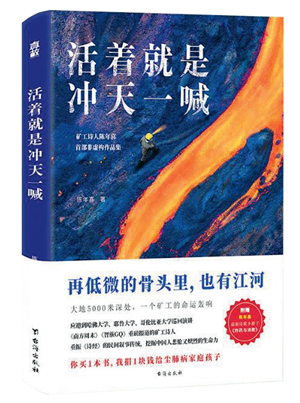傅聰 / 攝
陳年喜���,1970年生于陜西省丹鳳縣,在外打工��,寫(xiě)詩(shī)多年���。2014年出演紀(jì)錄片《我的詩(shī)篇》備受關(guān)注��。2020年3月��,被診斷為塵肺病�����。近期出版首部非虛構(gòu)作品集《活著就是沖天一喊》�。
從詩(shī)歌到非虛構(gòu),他記錄下中國(guó)社會(huì)變遷中的工人���、鄉(xiāng)村與蕓蕓眾生
○ 本刊記者 許曉迪
陜西丹鳳�����,秦之尾�����,楚之門(mén)����。商山自古名利路����,它連接南北,學(xué)子和商賈由此奔赴長(zhǎng)安�。橋底的丹江水從秦嶺而來(lái),黃濁中泛起星星點(diǎn)點(diǎn)的白浪��。岸邊的船幫會(huì)館建于清代,院內(nèi)的柳樹(shù)氣勢(shì)撼人���,拋下一片綠�。這是這座縣城最老的建筑���,路過(guò)好幾家“華萊士”���、“蜜雪冰城”和“正新雞排”后,突然闖入眼前�����。
陳年喜騎著摩托車(chē)駛過(guò)丹江�,平穩(wěn)地繞過(guò)每一條減速帶�����,開(kāi)向一片移民搬遷小區(qū)��。聒噪的蟬鳴中�,停好摩托車(chē),那是一輛網(wǎng)上淘來(lái)的鈴木王125��,一塵不染,锃亮反光����。這幾乎是他最昂貴的私產(chǎn),主要來(lái)發(fā)快遞����,給全國(guó)各地的讀者寄書(shū)。
屋里的地上放著幾摞書(shū)���,其中有他的第一本非構(gòu)作品集《活著就是沖天一喊》�����。陳年喜從網(wǎng)上買(mǎi)回來(lái)�,讀者從微信����、微博發(fā)來(lái)購(gòu)書(shū)信息,他簽好名����,題一句詩(shī),附贈(zèng)一張藏書(shū)票,再包郵寄出��,每本掙一點(diǎn)差價(jià)��。掙得的錢(qián)��,除了自己吃藥��,大部分用來(lái)家里的開(kāi)支��,尤其是兒子的學(xué)費(fèi)���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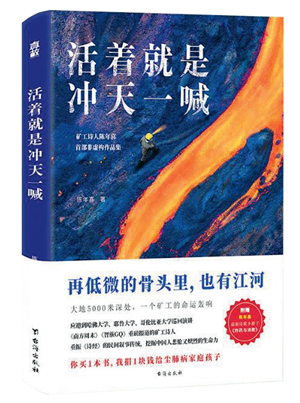 陳年喜的詩(shī)集《炸裂志》與第一部非虛構(gòu)文集《活著就是沖天一喊》。
陳年喜的詩(shī)集《炸裂志》與第一部非虛構(gòu)文集《活著就是沖天一喊》。
陳年喜一米八四的身高安置在一個(gè)小板凳上����。屋里悶熱,他把電扇轉(zhuǎn)到對(duì)面�,一滴汗順著耳朵消失在衣領(lǐng)中����,一兩聲輕微的咳嗽,隨著茶水送入喉嚨�。
今年4月,他寫(xiě)了一首詩(shī):“我已無(wú)法拒絕咳嗽/像無(wú)法拒絕到來(lái)的季節(jié)/季節(jié)正山高水長(zhǎng)/咳嗽正如影隨形/而這個(gè)春天/我寫(xiě)下的每一個(gè)字/都將風(fēng)吹云散……”
鄉(xiāng)村文事
2020年3月23日���,陳年喜在縣中醫(yī)院做了胸部CT��。農(nóng)歷春節(jié)后�����,他開(kāi)始一陣一陣地咳����,尾音帶著尖厲的金屬質(zhì)地。等結(jié)果時(shí)��,他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����,看陽(yáng)光透過(guò)玻璃,在地上墻上形成各種圖案���。一個(gè)三角形銳利的角�����,正對(duì)著他的腳�����。
16年的礦山爆破生涯��,已在他身上留下各種創(chuàng)口����,右耳失聰��,頸椎錯(cuò)位����。兩個(gè)小時(shí)后,大夫舉著片子告訴他:是塵肺���。
之前幾年,陳年喜的人生不斷翻轉(zhuǎn):他的詩(shī)在博客上被發(fā)現(xiàn)����,之后成為一部紀(jì)錄片的主人公之一���;他獲得“年度桂冠工人詩(shī)人獎(jiǎng)”��,上了電視綜藝����,為明星寫(xiě)歌詞�����;他跟隨攝制組出國(guó)�,登上帝國(guó)大廈,在哈佛�、耶魯演講�;他的后頸植入了3塊金屬,自此告別礦山����,在貴州一家旅游企業(yè)做起文案工作……
直到一場(chǎng)蟄伏了十幾年的“隱形礦難”突然降臨。“一張黑底CT影像膠片里/是我半生的倒影����。”確診10天后,他在詩(shī)中寫(xiě)道����。按照醫(yī)生開(kāi)的藥方�����,每月需要3000元的醫(yī)藥費(fèi)����,他自己把4類(lèi)中的兩種減去了�����。
最近一年多����,陳年喜一人住在縣城,這里有WiFi�����,也方便寄書(shū)�。愛(ài)人則留在老家峽河村。他沒(méi)事時(shí)會(huì)騎摩托回去�,公里表顯示68公里,山區(qū)彎彎繞繞����,騎得飛快,還是要跑兩三個(gè)小時(shí)���。走完了水泥路�,還有3公里的土路爬坡�,下雨時(shí)泥濘不堪。這些年���,攝制組與各路記者常常光顧這片荒山野地�����,長(zhǎng)槍短炮放在三輪車(chē)上����,一頓折騰����。
現(xiàn)在老家的地里種著白菜、豆角�����、辣椒、西紅柿����,基本不用買(mǎi)菜。還有一畝多的玉米����,因?yàn)橥恋刎汃ぃ划€只能打400斤�����,9毛錢(qián)一斤�����,種子��、化肥��、請(qǐng)拖拉機(jī)犁地����,加在一起500多,算下來(lái)�,收入是負(fù)數(shù)�����。除了老人�,大部分人已告別土地��。
30多年前����,人們“特別把地當(dāng)回事”�����,“漫山遍野都種�,還要去開(kāi)荒,東山也有�����,西山也有�����,種得無(wú)邊無(wú)涯”���。陳年喜家七口人���,種了10畝地����,刀耕火種�����,“沒(méi)一個(gè)吃閑飯的”�����,最多時(shí)有五六頭牛�,牛圈都裝不下。
1987年�,陳年喜高中畢業(yè),在家待了七八年��,主要任務(wù)是放牛��。牛漫山遍野地撒歡����,兩個(gè)往東跑��,兩個(gè)往西跑����,下雨還好��,可以跟著蹄印追蹤���;干燥的天氣�����,寄出的書(shū)中,陳年喜會(huì)題一句詩(shī)�,“只能聞著味兒去找”。
在山里有大把時(shí)間�����,陳年喜就拿著書(shū)躺在坡上看���,陳平原�����、黃子平的文章�,當(dāng)代畫(huà)家論,舞臺(tái)劇評(píng)����,“烏七八糟的,什么都看”�。他嗅到了沈從文和蕭紅身上的“野生性”,“寫(xiě)得不是特別合乎學(xué)院派的章法���,但里面有原生的氣息”�����。
他從高中開(kāi)始寫(xiě)詩(shī)����,喜歡北島����、芒克,甚至汪國(guó)真�����,現(xiàn)在看來(lái),“很庸俗�����、很老套”�,但發(fā)表了不少,一首詩(shī)的稿費(fèi)�,一般不超過(guò)10塊錢(qián)。
偏遠(yuǎn)的山村����,不少人家訂刊物,從《今古傳奇》����、《讀者》到《人民文學(xué)》�。丹鳳縣城,書(shū)攤林立�����,與當(dāng)下文壇無(wú)縫銜接�。隔三差五,陳年喜就會(huì)進(jìn)城買(mǎi)書(shū)。攤主不乏高人��,有的手捧《清通鑒》����,讀得忘乎所以;有的長(zhǎng)發(fā)披肩���,對(duì)愛(ài)倫坡�、里爾克如數(shù)家珍��。
他至今懷念那時(shí)候的從容余裕��,人們?cè)敢饣?年時(shí)間�,從頭到尾造起一個(gè)房子,“而不是先出去掙錢(qián)���,回來(lái)用錢(qián)堆積起一個(gè)房子”��。夜漫長(zhǎng)�����,他把一盞煤油燈放在床頭�,一口氣讀到天亮,鼻孔被熏成兩個(gè)黑洞���。
一次����,他從表姑那里借來(lái)一本《今古傳奇》���,上面有篇《玉嬌龍》�,改寫(xiě)自王度廬的《臥虎藏龍》��。他一夜讀完�,至今難忘。西域���,大漠����,胡人���,病弱,咳嗽�,北風(fēng)卷積百草斬……很多年后����,故事里的種種元素�,將在他的生命中一再出場(chǎng)。
 寄出的書(shū)中����,陳年喜會(huì)題一句詩(shī),(左)���。 附贈(zèng)一張藏書(shū)票
寄出的書(shū)中����,陳年喜會(huì)題一句詩(shī),(左)���。 附贈(zèng)一張藏書(shū)票
從礦山到皮村
1999年���,陳年喜的兒子出生。愛(ài)人身體不好�����,孩子要喝奶粉���,家中已山窮水盡���。這時(shí),《陜西日?qǐng)?bào)》發(fā)了他的兩首長(zhǎng)詩(shī)�,稿費(fèi)40元��,“救命錢(qián)一樣”����。
此后16年����,文學(xué)再也沒(méi)能給予他任何物質(zhì)回報(bào)。那年冬天�,陳年喜第一次去礦山,匯入浩浩湯湯的“打工潮”��。在河南靈寶�����,他一趟趟地把爆破下來(lái)的礦石或廢石拉出洞口�。礦洞低矮漆黑,他總是彎著腰�����,脖子上掛著手電筒�����。工棚由竹竿和木棍搭架����,外面蒙一層彩條塑料布。夜長(zhǎng)風(fēng)烈��,大家用被子蒙頭�,顫顫巍巍到天亮,早晨露出腦袋����,一床的雪花和枯草敗葉。
2000年春節(jié)��,陳年喜掙到520元����。這是他掙到的最大一筆錢(qián)。后來(lái)��,他改做巷道爆破���,秦嶺�����、祁連山���、天山�、阿爾泰山��、長(zhǎng)白山……幾乎走遍邊毛之地��。他的爆破史就是一部民用炸藥的制造演進(jìn)史�,一次次地和導(dǎo)火索的燃燒速度較量,和爆炸產(chǎn)生的沖擊波賽跑��。爆炸時(shí)濃煙滾滾��,常有人暈倒���,冷水潑不醒��,就拉出洞口讓風(fēng)吹�����,醒來(lái)后喝一大碗白糖水��,睡好幾天��。
16年里���,陳年喜一次次地歸去來(lái),每次都盡力拐到縣城的書(shū)攤上����,買(mǎi)幾本書(shū)刊,打發(fā)礦山上苦累荒涼的時(shí)間�。漸漸地,他發(fā)現(xiàn)書(shū)攤的根據(jù)地一再萎縮����,算命的、八卦的和學(xué)生輔導(dǎo)書(shū)籍取代了純文學(xué)書(shū)刊�;再后來(lái),書(shū)攤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(tái)�����。
2010年�����,陳年喜開(kāi)通了博客,發(fā)表詩(shī)歌��。“人哪怕看清了未來(lái)的路��,也有苦中作樂(lè)的權(quán)利��,就像其他的礦工閑暇時(shí)間會(huì)抽煙���、打牌�����,我就寫(xiě)詩(shī)���,都是情感的釋放。”他寫(xiě)過(guò)曹操����、劉備、陳勝吳廣�����、李自成��、林沖,寫(xiě)過(guò)蘇三起解�、白蛇傳、鍘美案�����、武家坡�����。他寫(xiě)秦腔:“活著就是沖天一喊/真情和真理���,皆在民間。”寫(xiě)自己的工作:“我撥開(kāi)大地的腹腔/取出過(guò)金銀錫鐵鎳銅/我把它們從幾千米的地下捕撈到地上/把這些不屬于我的財(cái)寶/交給老板再由老板借花獻(xiàn)佛/交給祖國(guó)和人民/一些副產(chǎn)我留下了——一點(diǎn)塵肺半身風(fēng)濕疼����。”
詩(shī)人、導(dǎo)演秦曉宇看到了這些詩(shī)�,為自己的紀(jì)錄片《我的詩(shī)篇》找到了第一男主角。2014年����,河南靈寶的礦洞中,攝像機(jī)拍下陳年喜打眼爆破�、處理巖石的工作場(chǎng)景,又隨他回到老家。梳妝臺(tái)上擺著一張結(jié)婚照�,相框里夾著一頁(yè)日歷,是陳年喜寫(xiě)給妻子的一首詩(shī):“我水銀一樣純凈的愛(ài)人/今夜�,我馬放南山,繞開(kāi)死亡/在白雪之上��,為你寫(xiě)下絕世的詩(shī)行�����。”

 上圖:《我的詩(shī)篇》中��,陳年喜在寫(xiě)一首給兒子的詩(shī)��。下圖:《我的詩(shī)篇》中�����,陳年喜給父親理發(fā)���。
上圖:《我的詩(shī)篇》中��,陳年喜在寫(xiě)一首給兒子的詩(shī)��。下圖:《我的詩(shī)篇》中�����,陳年喜給父親理發(fā)���。
2015年2月��,在秦曉宇的反復(fù)勸說(shuō)下��,陳年喜走下大雪茫茫的秦嶺��,穿著礦山上那身迷彩服�,在北京皮村的工人詩(shī)歌云端朗誦會(huì)上,念起他的代表作《炸裂志》:“我在五千米深處打發(fā)中年/我把巖層一次次炸裂/借此把一生重新組合/我微小的親人遠(yuǎn)在商山腳下/他們有病身體落滿(mǎn)灰塵/我的中年裁下多少/他們的晚年就能延長(zhǎng)多少�����。”
兩個(gè)月后�����,他的頸椎植入了3塊金屬���,從此告別礦山。幾個(gè)月后���,《詩(shī)歌之王》節(jié)目組找到陳年喜���,邀請(qǐng)他與歌手羅中旭搭檔,一個(gè)寫(xiě)詞�����,一個(gè)譜曲演唱���,和其他戰(zhàn)隊(duì)PK����。
他在北京住了3個(gè)多月,一星期寫(xiě)一首��,聽(tīng)了很多搖滾樂(lè)�,從崔健到周曉鷗,在歌詞上做批注��,“應(yīng)該唱出力量來(lái)”����,交出去后,都會(huì)消化成“青春的白馬王子風(fēng)”���。錄音棚里��,他坐在一旁�,隨時(shí)接受指令����,加字減字改字,“很折騰��、很痛苦”。他一共寫(xiě)了14首詞���,掙了3萬(wàn)多塊�。
2016年春天���,陳年喜來(lái)到皮村的“工友之家”���。這里魚(yú)龍混雜,失業(yè)者�����、藝術(shù)家�����、打工者雜處���,一兩分鐘就有飛機(jī)轟鳴而過(guò)。他住在一個(gè)廢棄的大雜院中��,七八個(gè)人一屋�����,一下雨就漏水,淋濕被子��。
每天���,陳年喜和工友們打開(kāi)北京各地的募捐箱�����,收集�、分揀里面的衣物���,消毒��、整合后再發(fā)往西部或非洲���。皮村也有愛(ài)心超市,每件衣服只賣(mài)十元八元�。他買(mǎi)了一大紙箱,足夠一家人穿十年有余�。
整個(gè)6月,陳年喜和工友們?nèi)プ稣{(diào)研�����,走遍了隱秘在樹(shù)林中的大小工廠,從家具����、玩具到電子產(chǎn)品。那個(gè)夏天����,他咳得厲害,架子床整夜搖晃���,最嚴(yán)重時(shí)���,他一咳,隔壁就捶墻��。那是他最困頓的時(shí)候�����,孩子讀高中���,每天花錢(qián)���,愛(ài)人租房陪讀,老家縣城兩難顧��,而巨大的北京城�����,茫然陌生如外星�����。
不遠(yuǎn)處的溫榆河不舍晝夜�,他常去那里散步,看著四季變換�,為這個(gè)“成就了多少香車(chē)寶馬/也成就了多少白刃與白旗”(《皮村》)的地方,為“腸胃里盛著粗食和白薯”(《奔跑的孩子》)的窮人的孩子��,為“被機(jī)床巨大的齒輪帶走”(《河流》)的張克林�����、劉三��、李安江們,寫(xiě)下組詩(shī)《皮村九章》�����。
那個(gè)冬天�����,陳年喜應(yīng)邀赴美��。他去了紐約的貧民窟�,去了舊金山的碼頭工會(huì)和“天使島”,也在時(shí)代廣場(chǎng)見(jiàn)證了特朗普出人意料地當(dāng)選��。在耶魯大學(xué)的演講中���,他說(shuō):“我看見(jiàn)合金的窗子�����、空調(diào)里的銅��、一切建筑物里的鋼���,還有那些金屬飾品��。那些我和工友兄弟們用汗水、淚水甚至姓名換來(lái)的金屬�����,建造了北京�����、上海���,抑或紐約�、波士頓。”他寫(xiě)下組詩(shī)《美利堅(jiān)記敘》���,審視一個(gè)資本全球化的世界:“二十年前秦嶺被一條隧道攔腰打穿/一些物質(zhì)和欲望一些命運(yùn)和死亡/從這頭輕易地搬運(yùn)到那頭/其實(shí)華爾街的意義也不過(guò)如此/在人們?nèi)ネ粗氐穆飞?又快捷了一程……(《華爾街》)”
憑借兩部組詩(shī)����,陳年喜獲得第一屆桂冠工人詩(shī)人獎(jiǎng)�,獎(jiǎng)金10萬(wàn)���。那兩年��,他沒(méi)掙到一點(diǎn)錢(qián)�����,這對(duì)他如同雪中送炭�����。
 2016年,陳年喜一家在北京皮村����。
2016年,陳年喜一家在北京皮村����。
現(xiàn)實(shí)的霜雪和命運(yùn)的霜雪不斷重疊
2017年過(guò)完春節(jié)�,陳年喜來(lái)到貴州綏陽(yáng)的“十二背后”風(fēng)景區(qū)做文案工作�。年薪5萬(wàn)���,管吃管住�。白天他坐在辦公室,寫(xiě)軟文�、講話稿和新聞稿;晚上就躺在床上���,在平板電腦上行云布雨。
他放下詩(shī)歌�����,開(kāi)始散文與非虛構(gòu)寫(xiě)作�。第一篇《一個(gè)鄉(xiāng)村木匠的最后十年》,6000多字�����,寫(xiě)了兩天��,主人公是父親�����,一輩子走鄉(xiāng)串戶(hù)��,腳踩百家門(mén)頭��,荒草中一座沒(méi)有完工的娘娘廟,是他生命最后的余響���。
3年里�,陳年喜寫(xiě)了50多篇散文與非虛構(gòu)作品���,每年掙得稿費(fèi)三四萬(wàn)元��,最終結(jié)集為他的第一本非虛構(gòu)文集《活著就是沖天一喊》��。艱辛的勞作�����,無(wú)常的生死�����,每一個(gè)故事����,都像陳年喜在礦山深處敲下的石頭一般���,堅(jiān)硬��、炫黑�。
有評(píng)論說(shuō),他“重振《詩(shī)經(jīng)》的民間敘事傳統(tǒng)�����,挖掘中國(guó)人悲愴又熾烈的生存力。震得人頭皮發(fā)麻”�。而實(shí)際上,這本書(shū)原本叫《一地霜白》�。這是陳年喜微信公號(hào)的名字��,“就像秋天的早上起來(lái),看到一地白霜���,百感交集”��。
他的詩(shī)中�����,霜����、白�、雪的意象總是反復(fù)出現(xiàn)�����。“我們一直工作在荒天野地的邊毛之地,每年見(jiàn)過(guò)最多的就是這些��。有時(shí)感覺(jué)自己的命運(yùn)���,也和季節(jié)的嚴(yán)酷如此匹配�。”陳年喜說(shuō)����,“寫(xiě)作的時(shí)候���,現(xiàn)實(shí)的霜雪和命運(yùn)的霜雪總是不斷重疊。”
過(guò)去詩(shī)中零星散落的工友們的故事����,在非虛構(gòu)的文體中得以延展豐盈���。“有的人特別能冒險(xiǎn),有的人特別講究吃�,有的人到哪里都要洗澡,有的人吹拉彈唱樣樣在行�。”有一個(gè)工友特別擅長(zhǎng)賭博��,在桌上隨意放一個(gè)打火機(jī)����,透過(guò)不銹鋼機(jī)殼的反光,能猜出每個(gè)人牌的花色�。陳年喜繪聲繪色地講起其中的奧秘,那是他已然揮別的歲月���。
2020年5月�,陳年喜從工作了3年的單位離職���。離職那天�����,他想起一些“再就業(yè)”的路子——到喀什的葉爾羌河邊去撿玉�����,那里有數(shù)不清的玉石����,十幾年前����,上好的一公斤墨玉只要300元��;或者到塔吉克斯坦干爆破工�����,那里急需中國(guó)工人的技術(shù)工藝���,簽3年協(xié)議�,如果順當(dāng)能掙90萬(wàn)���。最后��,雖然有不甘的悵惘����,他還是回到家鄉(xiāng),安心做了一個(gè)寫(xiě)作者���。
他還有很多故事想講��。每年夏天�����,愛(ài)人都會(huì)去黃河邊的韓城塬上摘花椒����。這是一份苦差,烈日暴曬�����,要帶很多水�����,樹(shù)上都是刺兒��,扎進(jìn)指頭�,挑也挑不出���。“椒客”們大多是女性�����,每天拼命地摘,一個(gè)月才掙得2000元�,“所有婦女從家走時(shí)都白白凈凈的���,回來(lái)后完全成了燒炭的”�����。
摘完花椒,愛(ài)人會(huì)順著黃河,去陜北摘蘋(píng)果���;另一些“椒客”則奔向西部的葡萄園�����,一直摘到大雪滿(mǎn)山——在大工業(yè)時(shí)代,她們?nèi)缤蝤B(niǎo)來(lái)回遷徙�,在機(jī)械無(wú)法施展拳腳的地方�,賺下一份寶貴的營(yíng)生�����。
還有那些民間樂(lè)隊(duì)�����,專(zhuān)為紅白喜事服務(wù)。他們無(wú)師自通��,吹拉彈唱����,身懷十八般武藝�。陳年喜參加過(guò)一個(gè)長(zhǎng)輩的葬禮,隊(duì)伍浩浩蕩蕩,河南來(lái)的樂(lè)隊(duì)吹起《百鳥(niǎo)朝鳳》�。上山路陡峭泥濘,他們吹得熱烈高昂����,鼓蕩人心����;走平路時(shí),又吹得哀傷沉痛,煽動(dòng)起滿(mǎn)腔悲愴。在這支隊(duì)伍里,有的來(lái)自解散的劇團(tuán)�����,有的是子承父業(yè),有的出道于“鄉(xiāng)村版”《星光大道》的比賽……每個(gè)人身上都可鋪展出一個(gè)精彩的故事�。
小飯館里,陳年喜吃著一碗9塊錢(qián)的青椒肉絲面�����,回復(fù)著買(mǎi)書(shū)讀者的微信�����。新書(shū)出版后,他平均每天賣(mài)出50本書(shū)�����,家里的快遞單����,攢了厚厚一摞。購(gòu)書(shū)人大多是城市的年輕人和知識(shí)群體���,從知識(shí)結(jié)構(gòu)到人生際遇,他們之間隔著一道寬闊的溝壑�。
在陳年喜看來(lái),相通的或許是一種人生的滄桑感��。“就像我們與杜甫隔了1000多年����,讀到他的‘三吏’‘三別’還是會(huì)觸動(dòng)。在一個(gè)劇烈變動(dòng)的時(shí)代���,唐朝老百姓的渺茫無(wú)助�,與今天的我們依然相通。”
2016年冬天��,陳年喜從西安坐慢車(chē)到貴陽(yáng)�,一夜無(wú)眠,寫(xiě)下一首詩(shī):火車(chē)跑著跑著天就亮了/一些人離家越來(lái)越近/一些人離家越來(lái)越遠(yuǎn)/窗外一閃而過(guò)的男人女人和孩子/這些早起的人苦命的人/晨風(fēng)掀動(dòng)他們的頭發(fā)和衣角/掀動(dòng)他們一成不變的生活/我喜歡這樣的境象/從小小的隔著晨曦的窗口/看見(jiàn)數(shù)不清的命運(yùn)/沒(méi)有什么能讓生活停下來(lái)/那些低低的訴說(shuō)包涵的巨大秘密/隨風(fēng)撒向高高的天空……
 左圖:2017年 ���,遼寧沈陽(yáng)����,陳年喜(中)參加紀(jì)錄片《我的詩(shī)篇》首映禮�����。
左圖:2017年 ���,遼寧沈陽(yáng)����,陳年喜(中)參加紀(jì)錄片《我的詩(shī)篇》首映禮�����。
右圖:2019年���,陳年喜簽售詩(shī)集《炸裂志》���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