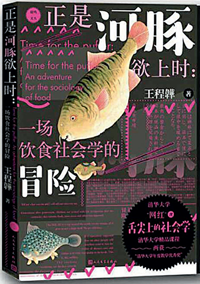2021年2月8日,王程韡在北京清華大學接受本刊專訪��。(本刊記者 侯欣穎 / 攝)
王程韡,1982年生于吉林公主嶺��。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副教授���、博士生導師�,美食愛好者����。2016年在清華大學開設“舌尖上的社會學”課程。近期出版《正是河豚欲上時:一場飲食社會學的冒險》�。
韡,音同偉���,意思是光明�、豐盛����。《詩經(jīng)·棠棣》里有這么一句“棠棣之華���,鄂不韡韡�。凡今之人�����,莫如兄弟”,翻譯成當代白話歌詞��,大概是:棠棣花兒開成片���,花萼花蒂多嬌艷。世上何物最珍貴��,山高水長兄弟情����。
上世紀90年代,家住吉林省公主嶺市的初中生王宇����,并不知道這些。那個年代����,速算風靡全國,身處東北偏遠小縣城����,教學資源匱乏,想學就得考試。王宇順利殺出重圍�����,進入當時罕見的30人小班�����。
考試更直接的刺激是重新發(fā)明了自我����。“王宇”這個名字,橫掃一大片��,以至要在后面?zhèn)渥⑸细赣H的名字�����,才能分清誰是誰���。他決定改個名�����,翻遍《新華字典》��,選了“程”“韡”兩個字�,“前途光明”。父母開明且心大���,就這么愉快地決定了�。
然后就陷入無窮的麻煩中����。高考涂卡���、銀行開戶���,第一步填姓名,就會遭遇“王程□”“王程*”“王程wei”等詭異搭配�;直到現(xiàn)在,他的身份證上�,“韡”是簡體的“韋+華”,學位證�、工作證上則是繁體,“這意味著在法律意義上����,世界上存在兩個‘老王’”��。
2021年�,是王程韡在清華教書的第九個年頭���。5年前�,他開了一門通識課“舌尖上的社會學”�����,后來獲得“清華大學精品課程”稱號�,每次一兩百頁的學術文獻、至少60分鐘的影像資料����,扎實硬核;但仍難掩“網(wǎng)紅”氣質�,選課和選上的比例,大概10:1�。
“舌尖”上到3.0版本,王程韡決定寫一本書���,給普通讀者��,也給兒子小菘���。這就是《正是河豚欲上時》����。
河豚�,大概是最讓人糾結的生物。大詩人兼“吃貨”蘇軾視之為人間美味����,做過東坡先生考官的梅堯臣卻以其肝、子����、眼睛���、脊血都有劇毒為由�����,勸大家別吃�����。“社會也是如此�。它無與倫比的復雜決定了我們很難用好—壞、善—惡去做一個單純的二分��。”王程韡在序言中說��,但作為社會中的個體�����,我們還是要去“冒險”認識它����,就像當年老饕們“河豚入市思拼命”一般好奇、認真����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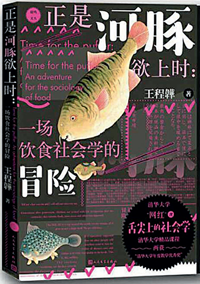 王程韡新作:《正是河豚欲上時:一場飲食社會學的冒險》�。
王程韡新作:《正是河豚欲上時:一場飲食社會學的冒險》�。
一場飲食與社會的“冒險”
寫這本書,王程韡給了兩個理由���,一個是長久以來對“科學技術學”理論��,特別是法國哲學家拉圖爾思想的關注�;另一個更接地氣也更“觸及靈魂”——來自一次ICU里的人生反思�。
嗜鉻細胞瘤��,“得了會壓迫腎上腺�,血壓奇高”��。在體育鍛煉蔚成風氣的清華���,作為一名園中“青椒”(大學青年教師別稱)�����,王程韡常年游泳�,偶爾血壓高一點�����,以為是運動過了量��。
等被查出得了這種名字奇怪的兇險疾病����,醫(yī)院的床位還要等號排隊����。王程韡決定回老家做手術��。手術是全麻���,推出來后,要在ICU里留觀48小時����。那一天是2014年12月31日,在所有人歡欣跨年的時刻���,他旁邊是正在搶救的病人����,頭頂是長明的燈��,每一秒都是煎熬�。
在可怕的清醒中,王程韡開始思考人生:“原來的研究還要不要繼續(xù)�?如果上人生中最后一門課,還要不要講以前的東西���?我是誰�����?我為什么會成長為今天這個樣子��?”
他的家鄉(xiāng)公主嶺�����,一個距離長春40公里的“十八線小縣城”���,在那個“學好數(shù)理化����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時代�,王程韡考上了清華電子系,胡吃海塞了一暑假��,以95公斤的體重邁入大學時代�。
在ICU病床上,王程韡回顧自己的前半生����,發(fā)現(xiàn)“每次打開記憶的閘門�,流出來的全都是吃的東西”——作為一個10歲就開始做飯的廚子,食物,是他建構自我�、發(fā)現(xiàn)社會、理解時代的一面透鏡�。
《正是河豚欲上時》(下文簡稱《河豚》)描寫的就是這一場飲食與社會的“冒險”。王程韡用“一魚兩吃”來形容這本書的兩種不同讀法�。
先看正文,就是一個個通俗故事�,貫穿著他自己從“小王”到“老王”一路與吃相伴的成長史:從家門口小賣店的“無花果”“蜜桃精”,到長春姥姥家的紅腸���、白菜卷和粉鴿子�;從“美國加州牛肉面大王”里一碗并不正宗的牛肉面�����,到“必勝客”里一疊高高的沙拉塔�;從在波士頓用魚片、豆腐片����、西紅柿和檸檬胡椒鼓搗出一鍋美國版酸湯魚,到升級“奶爸”后焦慮不安地給兒子小崧選奶粉����、做輔食��;從在深圳夜市里放飛自我地點一鍋砂鍋粥����,到躺在病床上虛弱無力地吃著各種病號飯……
再看尾注���,幾乎與正文等長��,延展出飲食背后的時代癥結�,關乎文化秩序�、世界體系、資本邏輯���、民族國家����、全球化……于是����,一杯喜茶就是一個世界,在它的兩端��,一邊是排起長龍�����、追逐網(wǎng)紅的消費者�����,一邊是在阿薩姆的茶園里捉蟲或是在非洲的大山里背咖啡豆的小孩�;就像一間麥當勞,從象征著美國生活方式的正宗洋快餐��,到被憤怒市民抵制的“國際超級鐵公雞”�,再到收容城市流浪漢、拾荒者的避風港�����,金拱門依舊���,它的涵義變遷����,卻是整個中國的變遷�����。
 “舌尖上的社會學”課堂上。
“舌尖上的社會學”課堂上。
用寫段子的勁頭備課
這樣的寫法����,自然是一場“冒險”。王程韡拉來人類學“大神”列維—施特勞斯來壯膽����。后者在《熱帶的憂郁》里絮絮叨叨地記錄下年輕時在亞馬孫叢林的探險經(jīng)歷,而這部看起來毫不“學術”的散漫游記���,已成為人類學的不朽經(jīng)典��。
但在中國學術界�����,很少有人這么寫��,這只“河豚”的誕生自然一路坎坷����。一波三折后�����,人民文學出版社欣然接手。王程韡決定將版稅捐贈給一所貧困地區(qū)的小學�,用作一年的營養(yǎng)餐費用。他和學生坦陳�����,《河豚》注定不會是暢銷書���,也許首印的8000冊就是極限。但一本小書也有自己的力量��,比如給一所學校一年的好時光���。
這也正是《河豚》試圖表達的:小人物依然可以以自己的方式�,認識和改變周遭的小世界��。舌尖上的社會學�,也是每個普通人的社會學。“我講了這么多我的故事����,你有沒有一種沖動,寫寫自己的故事呢�?”2020年秋天��,“舌尖”開到第四個年頭��,按照王程韡對自己的要求——一門課最多開5年��,到了該落幕的時刻�����。這一次�,他決定“任性一把”����,要每位同學提交一份不多于3000字的生命歷程敘事報告。
對王程韡來說��,教育是一件嚴肅且私人的事情�����,為此要勤奮備課����,“15分鐘必須爆個梗,要不同學就溜號了”。他拿出寫脫口秀段子的勁頭����,為此不斷從《脫口秀大會》的李雪琴那里“上貨”,甚至對她半決賽的稿子進行了詳細批注���。
“隔壁(北大)能培養(yǎng)出李雪琴���,確實比清華強。”王程韡感嘆�,“她的稿子有社會科學的學術底子����,又能把深刻變成段子和笑料。”相比而言�����,大多數(shù)學術寫作則“慘不忍睹”�����,處于“寫書—出書—送書—銷毀”的內(nèi)循環(huán)中��。即便是標榜通俗的寫作����,也是炒作媒體炒作過的話題��,隔著窗戶紙點撥一下�,“聽一聽����,貌似有道理,緩解了心中焦慮�,然后隨即忘了”。
他在圖書統(tǒng)計系統(tǒng)“開卷”上搜索“像××一樣思考”的書名����,科學家、哲學家����、經(jīng)濟學家、社會學家�����、人類學家����、法學家�,沒有不能“思考”的��。“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認知圖式�����,不會輕易改變����,所以也不可能像你一樣思考。你能做的����,是像每個普通人一樣思考�,然后用普通人能理解的方式講出來。”
《河豚》就是這樣寫出來的�����。“舌尖上的社會學”落幕后���,接檔的新課是“二次元醫(yī)學社會史”��,同樣來自王程韡對個人生命的追問��。課程大綱已出了一版�,涉及《鬼滅之刃》《火影忍者》《哪吒鬧海》《邋遢大王》等���,看題目�,中二與學術之魂都熊熊燃燒�����。他的少年時代在《哆啦A夢》《圣斗士星矢》《七龍珠》“老三本”的陪伴下度過��,長大后除了打磨廚藝�,最大的愛好就是“追番”。開這門課的目的��,“一來是讓醫(yī)學史變得有趣�����,二來是刺激一下漸漸滑入玄幻套路的國漫�,敢不敢正視一下我們這個豐富多彩的現(xiàn)實社會?”
 接檔“舌尖”的新課“二次元醫(yī)學社會史”�,涉及《鬼滅之刃》《火影忍者》《哪吒鬧?�!贰跺邋荽?/span>王》等中外動漫����。
接檔“舌尖”的新課“二次元醫(yī)學社會史”�,涉及《鬼滅之刃》《火影忍者》《哪吒鬧?�!贰跺邋荽?/span>王》等中外動漫����。
春節(jié)前���,王程韡在辦公室門上貼了一副新對聯(lián):“菘芥筆羹獻歲新�,瑄玉不琢侍祠頻����。”“瑄”是女兒瑄瑄,2021年1月1日凌晨出生���;“菘”是兒子小菘����,今年3歲�����。他說�,女兒要像古代的玉璧�����,璀璨明麗���;兒子則可以低調一點����,就像被譽為“諸蔬之冠”的菘��,清清白白����,不染功利心,民間俗稱大白菜��。
幾年前�����,他開了個公號“蘇菲的腦洞”��,即智慧(Sophie)的腦洞����。網(wǎng)友用“前途光明”的包袱送他網(wǎng)名“蘇潛光”����,他欣然接受�。公號上除了一些正經(jīng)或不正經(jīng)的學術探討,還記錄下一個名校“青椒”在學術與帶娃間鐘擺般搖蕩的真實生活����。
2020年,王程韡38歲���。這一年����,經(jīng)歷了疫情下的隔離����、網(wǎng)課的手忙腳亂、物價的節(jié)節(jié)飆升����,他在公號上定下未來的目標:做一點真正喜歡的研究,開一些名字不那么討喜的課����,時不時給自己和家人包頓餃子。還有��,趁著延過一次的海洋館年卡沒過期���,再多去看看被困在小房子里的企鵝�����。
 左圖:王程韡一家合影����?����!逗与唷芬粫?/span>中多次提及妻子大花與兒子小菘��。(本刊記者 侯欣穎 /攝)
左圖:王程韡一家合影����?����!逗与唷芬粫?/span>中多次提及妻子大花與兒子小菘��。(本刊記者 侯欣穎 /攝)
右圖:在個人公號“蘇菲的腦洞”里����,王程韡記錄下一個名校“ 青椒 ”在學術、做飯��、帶娃之間穿梭忙碌的日常生活����。
每個人都有一扇任意門
《環(huán)球人物》:你在書中提到了“無花果”���、“蜜桃精”、跳跳糖���,都是很鮮明的80年代食物����,這算是一代人共同的記憶�����。
王程韡:弗里德曼當年說“世界是平的”��,但根本不是��。世界分為中心和邊緣����,中心可能是北京、上海�����、紐約、倫敦���,但公主嶺肯定是邊緣的邊緣,所以我們才會吃到用蘿卜絲制成的假無花果���,而且吃得很開心��。這個世界的不均質從零食就可以看出來����。比如在北京看到可比克����,你會覺得這個超市檔次好低,但在很多縣城�����,可比克是最高端的薯片品牌����,放在最現(xiàn)眼的位置,哪兒有樂事呀?
《環(huán)球人物》:書中講到當代人為了吃得健康�����,從養(yǎng)生老湯到低溫慢煮����、輕斷食,不斷鼓搗新花樣�,為什么現(xiàn)在保健、養(yǎng)生的人越來越多�、越來越年輕?
王程韡:現(xiàn)代化轉型中�����,個人的商品化在所難免���。準備生孩子了����,女性要吃點葉酸�,男性要戒煙戒酒,胎教還要聽點古典音樂�����。每個人很早就明白,我是一個商品�,應該讓自己具有更多的價值。于是從考大學到找工作�,每一個能寫到簡歷、展露在酒桌上的東西�,都應該馬上積累�����。所以才會有養(yǎng)生的焦慮����,因為如果命都沒了,價值就直接歸零了����。年輕人不去思考整個社會結構帶來的壓迫,而是想通過一些可控的手段��,比如喝點枸杞菊花��,來實現(xiàn)更好的改變�,因為身體是很多人生活中碩果僅存的、能控制住的東西。
但我不想批判����,相反,這是一種合適的方式��。在過去����,馬克思告訴你,資本家欺負你����,你要沖到他的工廠,把機器都搗毀���;斯科特告訴你����,你就磨洋工�����,使用弱者的武器�。但現(xiàn)在����,對抗和逃避都是不現(xiàn)實的�。我們要找到一種與世界和解的方式,改變不了大社會����,還不能改變小世界嗎?如果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合適的方式�����,整個大環(huán)境說不定就改變了呢�����?
《環(huán)球人物》:你與世界和解的方式是什么��?
王程韡:知識����。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我很快樂�,這種快樂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大部分家長的育兒焦慮。我老婆懷小崧的時候�����,我就把8年制的婦產(chǎn)科教材看了一遍,之后幾乎所有東西就沒“坑”了�。
《環(huán)球人物》:書中寫到王小波,你很喜歡他�?
王程韡:我的文學素養(yǎng)極差,高中時看過的只有金庸小說和韓寒的《三重門》��。讀王小波已經(jīng)是念研究生了�����,但真的很喜歡���。你想做一個社會的傀儡���,還是一只特立獨行的豬?這個問題一直在�。
如果小波還在,我想告訴他�,我們活得很好。無論我們選擇請客吃飯����,讓一輩子沒上臺講話機會的自己���,在鄉(xiāng)親面前露一把臉、提一口氣��;還是選擇在夜市吃衛(wèi)生堪憂的路邊攤����,卸下偽裝,逃離內(nèi)卷化的996�����、007��,都可以找到一種突破秩序����、重獲自由的方式�����。每個人都有一扇任意門�����,讓我們從社會中脫嵌,先去里邊待會兒�����,從一個商品活回一個人�,然后帶著一份開心重回現(xiàn)實?!逗与唷穼懙囊彩沁@個過程:我們從社會結構的束縛下走出,打開一扇門��,透出一點光���。
《環(huán)球人物》:蘇潛光����?
王程韡:哈哈哈�。
(本刊記者 許曉迪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