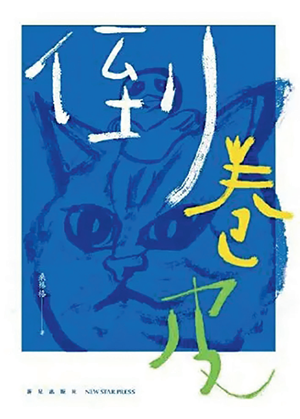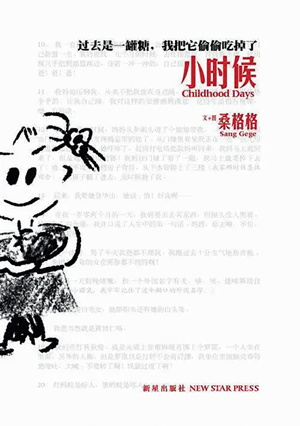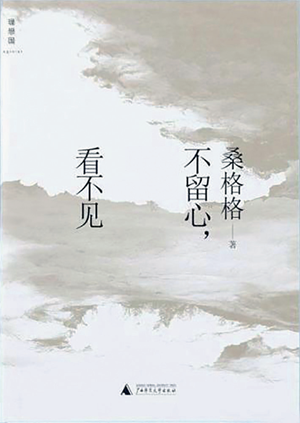桑格格����,1979年生于成都���,作家�、詩人���。曾從事演員�����、記者等職業(yè)���,著有半自傳體小說《小時候》《黑花黃》《不留心,看不見》等�����。近日���,首部漢語詩集《倒卷皮》出版���。
初夏的杭州��,濕熱氤氳���,桑格格生活的這片社區(qū),靜悄悄的�����。未到大門口����,就傳來她的招呼聲:“辛苦你跑一趟!”熱情的語氣中透露出一絲恬淡���。在她最新詩集《倒卷皮》里的一首詩中���,她說自己的體重和大一點(diǎn)的孩子差不多,見面一看����,比想象中更瘦:上身是寬松的半袖衫����,下身是紅褐色的寬松麻布褲��,頭發(fā)梳到腦后扎成辮子�,臉小而瘦削。
詩中的她���,童真��、詼諧,有時帶有成都話腔調(diào)����,她寫《磕頭》:“磕著磕著/愣在蒲團(tuán)上/我忘記/磕到第幾個了。”而眼前的她����,說話字正腔圓,時而眉頭緊鎖��,若有所思���;時而眉眼舒展�����,眼里放光��,讓人覺得有兩種能量很強(qiáng)的個性在她身體里較勁�。“我是一個與我的文字反差很大的人。”她對《環(huán)球人物》記者說�。“桑格格”是她以前當(dāng)記者時的筆名,“不是還珠格格的格格���,而是格格不入的格格”��。起初��,這部詩集叫《往寂靜處走》��,她想“躲起來”����。編輯給她選了《倒卷皮》這個名字�,意思是生活就像是手指上的“倒卷皮”一樣:要處理它,不扯不行�,但扯得不好又會出血。
 桑格格給讀者簽名。(本刊記者 劉瀟 / 攝)
桑格格給讀者簽名。(本刊記者 劉瀟 / 攝) 好詩一定是自我的
桑格格在坐榻上盤腿斟茶�。她泡的三道茶,味道不同:青澀�、微苦、甘甜����。茶碗是一個陶藝家朋友做的炻器。曾摔碎過�,又被“縫合”了。她的語氣一直淡淡的�����,讓人很難想象這是十多年前以一本《小時候》而聲名鵲起���、個性十足的文藝女青年。那時的她�,有著太多的熱情無處安放,個性多面���,像個“魔方”����。
“我是被詩拯救了。”桑格格平靜地說����。
2007年,半自傳體《小時候》出版���,桑格格一舉成名���,成為文壇中不可忽視的川派女作家。但成名也“劫持”了她的人生:她被迫接受“被作家”的命運(yùn)�,毫無頭緒地開始學(xué)主流作家如何寫小說的,毫無快樂可言�����。有一次���,一篇5000字的文章���,她硬生生磨了半年。她“走入了一個死胡同”��。
2010年前后�����,她得了抑郁癥,陷入苦思��,日子過得很沉重��、很緩慢��。為了排解擁塞的心緒�,她想到什么就寫下來,看到什么就記下來���。漸漸地�����,她回頭看心里灰暗時寫出來的東西����,竟發(fā)現(xiàn)并不沉重�����,甚至很輕松詼諧�����。寫作包袱一下就丟開了��。隔擋在她與文字之間的那堵墻越來越薄�,直到消失。
2016年�,病情好轉(zhuǎn)。她漸漸明白:自己的抓地性很強(qiáng)�����,需要緊抓生活����。“與其寫虛構(gòu)作品,我對掉落在地上的紐扣如何滾動更感興趣�。”放松下來,心中的詩便浮了上來�。
在《夢里的人》中,她寫自己抑郁時的狀態(tài):“夢見一個女孩/帶著哭腔走進(jìn)我的臥室/我失戀了�����,格格�����。/我努力睜開眼睛看她/但是無法做到,只好說/你先去客廳坐一會兒/我穿上衣服就出來好嗎��。”她撿到山路蟬蛻����,由此寫到秋日愛情:“他沒要/說這個太脆弱了/怕自己收不好”;她寫生活中的無奈卻令人忍俊不禁:朋友為了見男人而減肥三十斤�,但“男人避而不見/她只有/輕飄飄地/回來了”;她也能像孩子一樣使用“通感”�����,在《最早的春天》中寫道:“……并沒有戴眼鏡/居然能看清楚/雨滴打在遙遠(yuǎn)的/池塘里���,一圈一圈/漣漪擴(kuò)散得非常清晰”����。
5年后的今天����,第一部詩集《倒卷皮》誕生。詩集是她被詩拯救��、找到自我的展現(xiàn)��。在她心中�,好詩一定是自我的,都是喃喃自語的�����。“我懷疑‘文以載道’�����,文學(xué)不是觀點(diǎn)的傳聲筒����,它應(yīng)該有自己的獨(dú)立性。”現(xiàn)在的她活得很放松�,有時某個朋友會過來專門和她一起發(fā)呆,完全不用擔(dān)心對方不舒服��,一直放松到“蠢”的狀態(tài)�。她認(rèn)識一個畫唐卡的藏族小伙子,兩人一見面就傻笑����,比誰的腿粗��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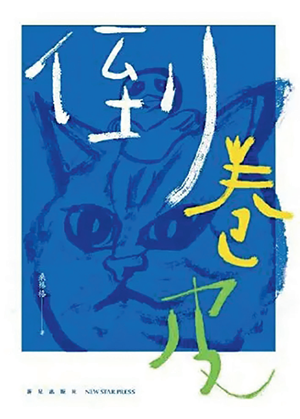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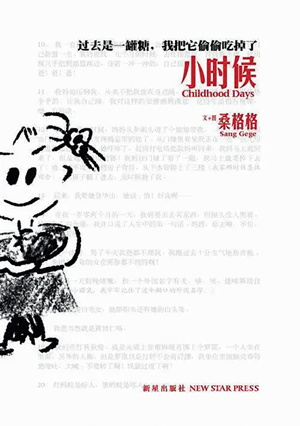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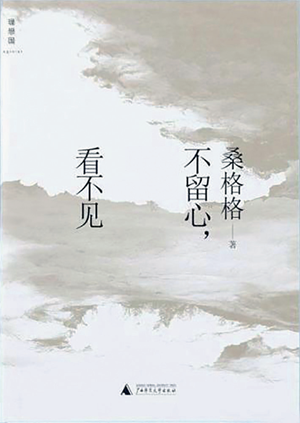 桑格格的作品:《倒卷皮》《小時候》《不留心,看不見》���。
桑格格的作品:《倒卷皮》《小時候》《不留心,看不見》���。 沒有純真就沒有力量
成名以后���,曾有記者問過桑格格,她寫作與文化的關(guān)系�,她回答:沒關(guān)系。“我不希望被異化成‘文化人’����,我希望自己是一個真實(shí)的普通人。”
在420廠第一幼兒園當(dāng)小“大姐大”也許是她人生最高光的時刻��。小學(xué)二年級時���,父母離異�,她的心像一葉孤舟在急流中漂蕩����,直到長大后撞見了“九色鹿”。當(dāng)時,“九色鹿”是廣州美院老師�,眼睛大而圓,儒雅而英俊�����,像那只自帶光芒的鹿����。這個外號是桑格格起的�。走在學(xué)校里,女生們總是對著他偷瞄竊喜���。桑格格住進(jìn)他9平方米的小屋內(nèi)���,安頓下來,尚無頭緒�。
2004年的一天,桑格格與朋友聊天��,童年回憶一下撬開��。她開始以“完全是噴涌的狀態(tài)”在網(wǎng)上寫小時候的事��。一天1萬字,她寫小時候看的動畫片�、做的游戲,上世紀(jì)80年代的氣息撲面而來����,濃郁而輕松,一下就捕獲了大批“80后”的心����。
3年后,桑格格的半自傳體小說《小時候》出版����。當(dāng)時市面上從未有過這種形式的文字:通透、有趣���、純真��。一經(jīng)出版��,月內(nèi)售罄�����,隨即再版�,又售罄,總共再版了4次����。她把骨子里的熱烈、大膽�����、童真甚至是一絲匪氣倒進(jìn)了文字中����。各大媒體開始關(guān)注這位闖入文壇的成都姑娘�,關(guān)于她在北上廣的“浪跡史”、與丈夫“九色鹿”的愛情故事也像傳奇一樣在網(wǎng)上流傳�,為人津津樂道。
一只腳邁進(jìn)文化圈�,期待與目光便接踵而來,逃也逃不掉���。桑格格害怕陷進(jìn)去�����。“文化是一個龐大的漩渦����,人要進(jìn)去就要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,不被文化帶著走�。被文化帶走了,純真就也走了�。沒有純真,我就沒力量����。真正的藝術(shù)都是一個人在天性中奔跑,直接把最源頭的東西摘下來��。我就想當(dāng)一個真實(shí)一點(diǎn)���、與文化不沾邊的普通人����。”她說�。
抑郁期間,她的寫作幾乎停滯�。直到2014年,《不留心�,看不見》出版,延續(xù)了《小時候》的半自傳體風(fēng)格���。她寫彩蘋����、丑舅舅、我的420廠……那些最普通的�����、微不足道的人和事����,在她的筆下妙趣橫生。有人評價:“她是彪悍的存在主義者�����。”也有人說:她只是用很輕的筆觸去寫很沉重的東西�����。
桑格格一直想著如何擺脫身上的標(biāo)簽���。平日里,她讀書����、畫畫�����、彈琴���、寫作,偶爾參加文化沙龍�����。
在寫《倒卷皮》的詩句時�����,她從不考慮“我這句話厲不厲害����,能不能唬住人”。有個編輯總是說:“格格���,我想從你的詩里找點(diǎn)金句�����,可一句都找不到�����。”她回答說:“我要是老寫出金句��,說明‘乳腺增生’——沒化開���。我一定要把自己化得開開的����,每一句都普普通通����,以純真的方式攤開來。”
《倒卷皮》出版的那一天�����,她說不想再寫了����。她太渴望活在一個更深一點(diǎn)的東西內(nèi)部�,不被刨出來����,不被發(fā)現(xiàn)��、不被貼上任何標(biāo)簽�����。
 桑格格在成都舉行的《倒卷皮》首場讀者見面會上�。
桑格格在成都舉行的《倒卷皮》首場讀者見面會上�。 凡事都攤平得像一張大餅
“其實(shí)沒有什么詩人,只有一個充分活著的人�����。充分活著的人會拿一桿搟面杖把自己搟開�,去承接更多的詩意。”桑格格坦言��。凡事都攤平得像一張大餅����,即便世事難圓滿,至少在內(nèi)心“攤平”����,去接受��。
小時候她與母親相依為命��,常年缺失父愛����,漸漸與父親有了隔閡��。直到3年前�����,父親來杭州看病���,她看到了父親的好���,心中竊喜:原來我也有爸爸。這事就在心里“攤平了”�����。
“如果不攤平�,心里過不去�����。”桑格格養(yǎng)成了換位思考、寬容他人的習(xí)慣����。她趕公交,司機(jī)看了下反光鏡����,猶豫兩秒還是開走了:“我不怪他/他猶豫過”。一份綿延多年的情愫�����,若隱若現(xiàn)地存續(xù)著�����,她在詩《黃了十次》里頭說:“你家樓下/是一排銀杏/……/每年都在心里/變黃一次”�。凡事攤平,就過去了���,回到家中�����,擼那只叫“老三”的漂亮胖貓�。
她也努力幫別人把事“攤平”。武漢疫情時�����,她加入了在線志愿者團(tuán)隊(duì)���。“因?yàn)槲⒉┯幸稽c(diǎn)閱讀量”�����,她就讓需要救助的人在她的微博下方留言��,讓更多人看到���。那段時間,她在團(tuán)隊(duì)中負(fù)責(zé)外聯(lián)�,找醫(yī)院、找物資���、找捐助����,做心理疏導(dǎo)���。“每天都像個戰(zhàn)士���。”但她感到人生已被無限展開了。
疫情中����,一個失去母親的姑娘對桑格格觸動很大。志愿者們讓她當(dāng)晚先別一個人回家�����,可這個姑娘平靜地說:我還是要回家��,因?yàn)?ldquo;冰箱里還有剩菜沒吃”��。在經(jīng)歷了如此巨大的悲傷后�,姑娘考慮的事情是“生活還要繼續(xù)”。桑格格說��,她要做的只是疏導(dǎo)�����、“攤平”。“攤平了”�����,就不怕了��。
桑格格停頓一下��,接著說:“通過做志愿者�����,我發(fā)現(xiàn)我們離這個世界沒有那么遠(yuǎn)���。當(dāng)你起心動念的時候����,你已經(jīng)在做了�。”話音未落,她目光低垂��,一人到陽臺���,久久站立�,“老三”蹲在玻璃移門后看她。(本刊記者 劉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