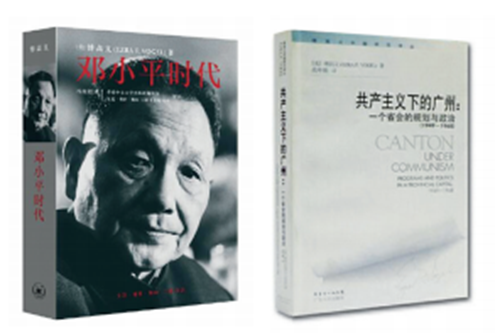傅高義����,1930年生,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���,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���。1950年畢業(yè)于韋斯利大學,1958年獲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�。精通中文和日文,著有《日本第一》《共產(chǎn)主義下的廣州》《領先一步:改革開放的廣東》《鄧小平時代》等著作�����。2020年12月20日去世����。
2020年12月20日,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因病去世��,享年90歲�。在美國��,他同時有“日本先生”和“中國先生”之稱。1979年���,他出版《日本第一:對美國的啟示》����,在日本高居暢銷榜榜首��。2011年�����,他傾10年之力寫就的《鄧小平時代》英文版在美國出版���,《紐約時報》書評稱之為“迄今為止對中國驚人而坎坷的經(jīng)濟改革之路最全面的記錄”���。
外交部發(fā)言人汪文斌在新聞發(fā)布會上表示,傅高義教授是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���,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�,中方對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����,對其家人表示誠摯慰問�。傅高義教授為促進中美溝通與交流�����、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���,我們將銘記他為推動中美關系發(fā)展所作貢獻�����。
“在中國研究中國”
傅高義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學術顧問��。中心主任吳心伯教授與他有20多年的交往����,稱他“有濃厚的中國情結”��。吳心伯告訴《環(huán)球人物》記者:“傅高義對中國的研究可以做一個形象的概括�����,就是‘在中國研究中國’�����。很多美國學者不是這樣��。他們研究中國時�����,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國�����,用美國的概念�、范式或價值觀來評判中國。傅高義不是這樣�。他還是希望盡可能地從中國的角度,從中國自身的環(huán)境和條件出發(fā)��,來理解中國的改革�����、發(fā)展�、變化。”
傅高義來自俄亥俄州一個小鎮(zhèn)的猶太人家庭��,從俄州韋斯利大學畢業(yè)后,1958年獲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��。1961年�,31歲的他被漢學家費正清選中,來到哈佛東亞研究中心�。當時,為他上中文課的是“漢語言學之父”趙元任的長女趙如蘭���。“她在語音上要求很嚴格���,所以我們這批學生比別人教出來的水平應該更高一點。”
直到晚年�����,傅高義經(jīng)常堅持以中文接受采訪�。人民日報原駐美首席記者溫憲回憶:“在采訪過程中,傅高義的漢語詞匯表達并非完美����,但足以清晰、坦率地表述他的觀點��。他說�,‘真正的朋友應該坦率交談��,實事求是’�。”本刊記者2013年在北京采訪傅高義����,當時他臉上掛著的熱情�����、和善的微笑�����,以及一口流利的中文�,讓記者有一種與中國學者暢談的錯覺。
 左圖:2013年4月��,傅高義(左三)在北京參加歐美同學會組織的“鄧小平時代與未來三十年”研討�����。
左圖:2013年4月��,傅高義(左三)在北京參加歐美同學會組織的“鄧小平時代與未來三十年”研討�����。
右圖:2015年9月7日����,傅高義接受溫憲采訪時合影。 傅高義的中文名也是他自己取的。他的英文名是埃茲拉·費韋爾·沃格爾���。他說�����,沃格爾是個德國姓�����,在德語里的發(fā)音很像中文的傅高��,英文名的第一個字母是E��,取其諧音選了義字���。“我知道在中文里,‘義’意味著很高的道德標準����,這正是我想追求的。”
1963年��,傅高義在香港進行了一年的研究����。那是當時西方學者唯一可以近距離研究中國的地方����。在香港�����,他能讀到《南方日報》《羊城晚報》《廣州日報》���,并請了一名剛從廣東到香港的年輕人做助手。“我看了1949年到1963年幾乎全部的《南方日報》�,他也跟著看,我有不明白的就問他����。比如我看報紙說‘反對×××’,就問他是什么意思�����,背景是什么����,他很詳細地告訴我�。特別是有關土改的經(jīng)驗���,最開始的政策是什么�,幾個月后政策又變成了什么����。”
1969年,傅高義完成了他第一部關于中國的作品《共產(chǎn)主義下的廣州》�。這部作品拋棄了西方學者的偏見,描繪中國的本來面貌�,在美國學術界產(chǎn)生了廣泛的影響。費正清稱之為“社會學家們從外部世界研究共產(chǎn)主義中國的杰出范例”�����。
吳心伯說�����,傅高義非常注重調研���。1958年以來���,他每年都要訪問亞洲�����,也經(jīng)常來中國�。“上世紀80年代他研究中國改革開放��,就在廣東待了一段時間��。”從1987年6月到12月���,傅高義在廣東實地調查了70多個縣��。1988年夏季�,他又在廣東調研了3個星期����。1989年��,他完成《領先一步:改革開放的廣東》�����,這是外國學者研究���、報道中國改革的第一部著作���。它和《共產(chǎn)主義下的廣州》共同構成了外國學者筆下的廣東當代史�。這次廣東之行���,傅高義的妻子艾秀慈也陪伴在他左右�。艾秀慈是美國凱斯西儲大學人類學者��,會講廣東話����。傅高義在《鄧小平時代》一書的扉頁上第一行就寫道:“獻給我的妻子艾秀慈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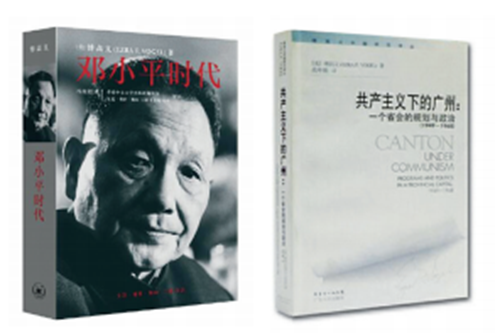 傅高義著作《鄧小平時代》《共產(chǎn)主義下的廣州》�。
傅高義著作《鄧小平時代》《共產(chǎn)主義下的廣州》�。 “你想解決的問題是什么?”
與傅高義有交往的中國人����,往往都會談到他對中國的友好感情。多次專訪傅高義的溫憲說:“他是一位活到老��、學到老的謙謙君子�����;他是一位頭腦冷靜、視野開闊����、仗義執(zhí)言、堅守節(jié)操的中國問題專家��;他是一位純粹意義上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��、好朋友�。”
溫憲回憶,2015年9月7日傅高義在位于哈佛校園的家中接受采訪�����。家中書房辦公桌右手處擺放著《習近平談治國理政》一書英文版�����,還有一本中文版的《谷牧回憶錄》及各種中�、英文紙質資料���、光盤和便箋����。屋中壁爐臺面上并排擺放著五張有著數(shù)十人合影的“全家福”照片,照片上方懸掛著一幅有著東亞傳統(tǒng)文化特色的畫作��。
傅高義談起了自己對中國變化的切身感受�����。他說:“我給你講一個例子���,一個月以前�����,我在重慶生病���,需要手術,在一個醫(yī)院待了五六天�����,手術很成功�。醫(yī)護人員剛開始不知道我是誰,就當我是一個普通外國人��。他們的醫(yī)療制度、醫(yī)護水平和美國差不多了�。我第一次去中國是42年前,當時看到醫(yī)療設備不行����。通過中美兩國間這么多年交流和相互學習,現(xiàn)在的情況好多了�。這就是中美兩國交流、發(fā)展的好事���。這種交流應該繼續(xù)下去��,因為這是互惠的����。”
北京外國語大學區(qū)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師陳征曾在哈佛大學受教于傅高義���。她告訴《環(huán)球人物》記者:“我認識傅高義教授時���,他早已退休。那時他已經(jīng)80多歲�,但只要是關于中國的講座,都會來參加���,還喜歡在講座結束后留下來參加冷餐會����,跟我們這些中國學子聊聊天�。有一次我們在肯尼迪政府學院辦了個講座,那里有個大坡�,老先生騎著自己的小自行車沖過來,我們看著他快速地沖下斜坡�,像個年輕人那般雀躍。”
“我剛到肯尼迪學院時有些迷茫�����。在一次冷餐會上遇到傅高義�,我問他該做什么研究。他說:‘你想解決的問題是什么�����?’我當時一聽有點暈����。我們過去做學問往往非常宏觀,看到大方向就開始整理材料����。但美國的教授往往會以小見大���,先找到一個問題,一旦能解釋清楚���,也就推動了理論創(chuàng)新�。這是老先生給我上的第一課��。”正在寫《鄧小平時代》的傅高義時間非常寶貴���。“第一次去他家討論論文����,我發(fā)現(xiàn)他的時間是以15分鐘為單位的�,每15分鐘就有一個訪客。我前面是位日本議員���,后面是位大咖����,而我還是個在摸索學術研究之門的學生�����。但每當我希望討論問題,他總是很慷慨地擠出時間見我�。那時���,我對美國總統(tǒng)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很感興趣�,想研究他們����。傅高義先生說他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,但愿意盡力幫我聯(lián)系他在華盛頓的朋友們����,讓我采訪他們。”陳征對學術研究道路有些不自信�,傅高義說:“你年齡不大,你看看我今年多大了�,你在我面前就是年輕的小朋友。我仍在寫書���,你只要想做研究����,什么時候都不晚。”
吳心伯說�����,傅高義總是以平等的態(tài)度與中國學者交往��,向來注意傾聽中國學者的見解��,虛心地交換意見��,不像有些美國人那樣自以為是��,居高臨下�����。他曾去哈佛演講�,傅高義專門安排他與哈佛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座談。“傅高義很注重與中國學者包括政府官員的交往��。他有句很形象的話:研究中國要搞關系��。他知道在中國文化里關系的重要性�����,如果不跟中國人交朋友,就很難真正理解他們�����。”
1997年����,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哈佛大學發(fā)表演講��。“那件事就是傅高義一手安排的�。當時,哈佛方面也有不少反對意見���,對中國的所謂‘人權’等有看法�。傅高義強調�,江澤民作為中國領導人,治理這么大的一個國家不容易�����,我們應該聽聽他怎么說���。從這一點可以看出�����,他不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國�����,而且盡可能地希望從中國的角度出發(fā)���,在了解和理解的基礎上研究中國���。”吳心伯說。
“他對中美關系挺憂心”
在漫長的一生中�,傅高義一直積極推動中美交流。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(tǒng)后���,傅高義和多位中國問題專家致信尼克松:“現(xiàn)在是跟中國接觸的好機會”���。他和學者們還向時任總統(tǒng)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。1993年�����,他應邀出任國家情報委員會東亞情報官。他說:“那段經(jīng)歷對我做研究幫助很大��,時任駐華大使芮效儉的報告我也能看到�。”
2000年退休后,他開始了研究和撰寫《鄧小平時代》的十年工程��。他曾向本刊記者解釋:中國的變化改變著世界���,沒有一個領導人(鄧小平)對世界的發(fā)展有過如此的影響�����。出版該書中文版的三聯(lián)書店總編輯李昕說:“傅高義告訴西方讀者,也包括中國讀者���,中國的發(fā)展道路從哪里來�����,向何處去����,他幫助讀者理解了我們所親歷的中國改革時代的昨天和今天�。”
不過,近年來���,傅高義對中美關系挺憂心��。吳心伯說:“2018年�����,傅高義教授應邀到上海出席‘紀念中美建交40周年’研討會�����,專門抽時間到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做了一場關于中美關系的報告���。當時的題目叫對中美關系40年的思考�����。那天���,他花了很多時間講鄧小平對改革開放和中美關系發(fā)展的貢獻。我覺得�����,他對中美關系40年的發(fā)展是很留戀的,對中國4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也很欽佩�。當時,特朗普已經(jīng)上臺�,中美關系大的氣氛發(fā)生了變化?����?紤]到特朗普上臺以后執(zhí)行的限制中美人文交流等措施����,中美關系不斷受到削弱,傅高義對中美關系的走向還是挺憂心��。”
2019年7月初��,傅高義作為5位執(zhí)筆人之一���,起草《中國不是敵人》公開信在《華盛頓郵報》發(fā)表。這封寫給美國總統(tǒng)和國會的公開信��,反對美國采取與中國對抗的政策�����。他最后一次出現(xiàn)在中國觀眾面前是2020年的12月1日。他在參加北京香山論壇視頻研討會時表示��,拜登當選美國總統(tǒng)��,給中美關系帶來了新的機會����。但美國應該承認中國對世界的貢獻,公平地對待中國����。
像傅高義這樣真正了解中國的“知華派”,美國還有多少��?吳心伯說:“不多了���。不要說是他這個年齡的��,比他晚一輩的70歲左右的學者����,現(xiàn)在也已經(jīng)逐漸淡出第一線了�。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正在發(fā)生明顯的代際轉換。”在吳心伯看來����,傅高義的研究風格“代表了對中國的理解�����、尊重和交往”�,而美國現(xiàn)在年輕一代很多人“不愿意去理解中國�����,不愿意尊重你”�����。受美國國內政治氣氛影響�,美國很多人變得小心翼翼,有些強硬派根本就不來中國���。“這些人現(xiàn)在越來越多地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�����,對中美關系的影響是負面的。”
 青年學者陳征在哈佛大學學習時與傅高義合影��。
青年學者陳征在哈佛大學學習時與傅高義合影��。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發(fā)推文緬懷傅高義:“他對中國的智慧和見解不僅對研究該領域的人有不可估量的價值,對整個世界來說也是如此�。”在尊重、平等�、交流基礎上的傅高義式“知華”,這是人們如今最為懷念的�。(本刊記者 崔雋 田亮 本刊駐美國特約記者 安迪)